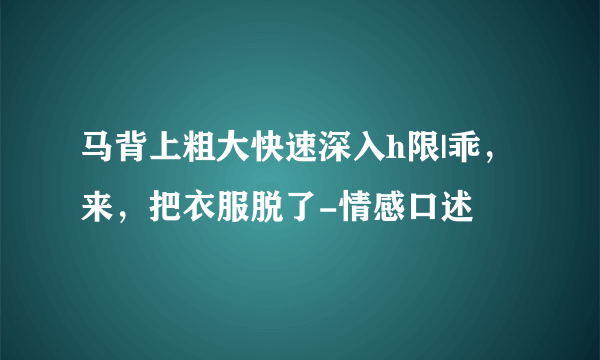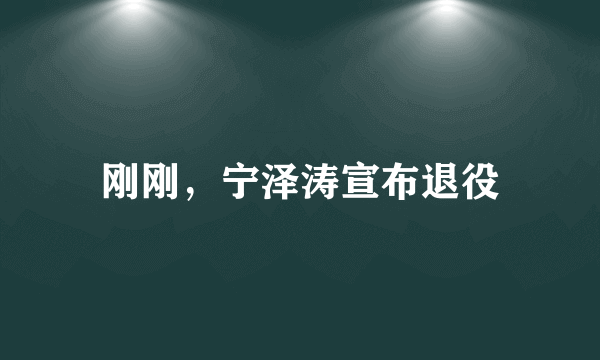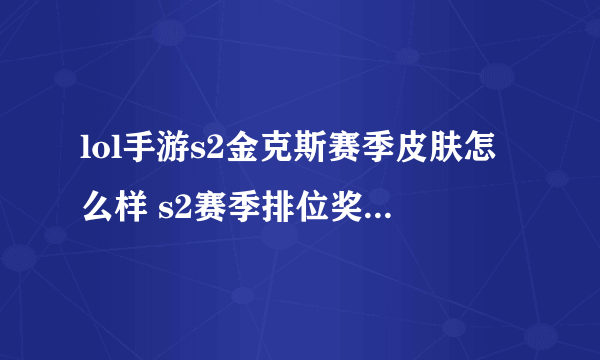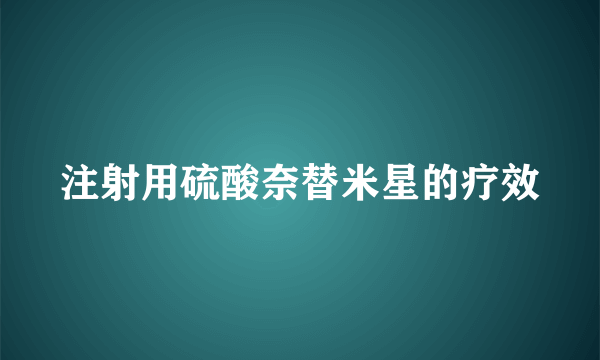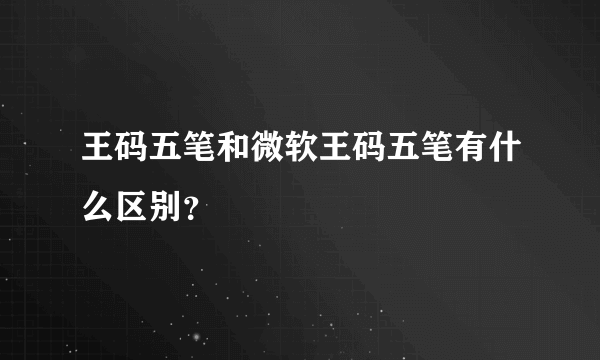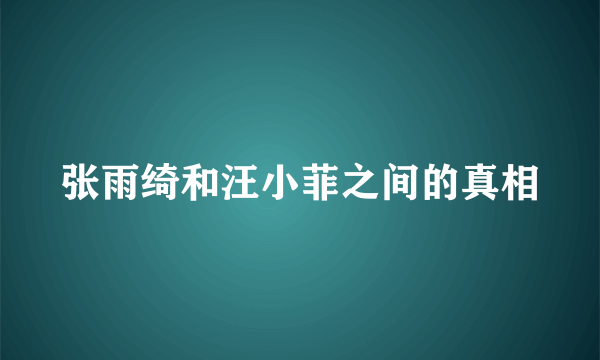英那河日夜流淌,不息的波涛,淘洗着鲜为人知的故事。
让我们把目光投向庄河市吴炉镇红旗水库近旁卧鹿山东端王学沟的东坡,看看那几座野草丛生的坟墓。没有墓碑,没有参天的古树,在早春的阳光里,这里显得格外肃穆。在这片墓地里,长眠着一位居住在英那河下游满族舒穆录氏引为骄傲的祖先———多隆阿。
多隆阿简介
多隆阿(乾隆五十九年1794—咸丰三年1853)字雯溪,又字文希,舒穆录氏。祖居长白,康熙二十六年徙岫岩。高祖讳花色,父讳德普,为长子。年十九补博士弟子员。道光十七年丁酉举拔贡,时年三十六岁。不屑于揣摩括帖时文,为学专肆力于经。尝为礼部郎何维墀幕宾;后何维墀出守山西平阳,聘多隆阿为山长掌书院事,有衡文与治狱之才,受何赏识。咸丰三年八月,太平军攻破平阳城,多隆阿协助守城,事败被杀,享年六十岁。著有《易原》、《易图说》、《易蠡》、《毛诗多识》、《慧珠阁诗钞》、《慧珠阁文钞》、《慧珠阁诗话》、《阳宅拾遗》、《地理一隅》等,为满族文人中之博学者。
多隆阿的传说与掌故
在多隆阿后人居住地———原小孤山满族镇(现已并入吴炉镇)孙堡村,记者走进了多隆阿第五世孙、今年81岁的孙庆先的五间茅屋。孙庆先老人如数家珍讲起了关于多隆阿的传说。多隆阿任盛京书院山长时,写《易原》几易其稿总不满意,仲秋的一天晚上,他来到小河沿公园,坐在魁星楼下休息。猛然,他听到魁星楼上有人在谈《易经》,听着听着,时间不知不觉过了半夜。凉风袭来,他止不住咳嗽了一声,魁星楼上的谈经声戛然而止。回去后,多隆阿根据听到的内容对原作进行反复删改,终于写出见解独到、多有神来之笔的《易原》。又传说当年多隆阿在任莲宗寺书院院长时,朝鲜学者李某游学盛京,到书院考校学识。多隆阿说,天文地理、史记纲鉴、诸子百家、诗词歌赋任选。李某意在考校诗歌,便起句云:“辽东春色已凋零”。在场的张绣江、何晓枫吟出二、三句:“惟有此间柳尚青。岂是天公分厚薄”,多隆阿则以一句慷慨激昂的“严霜焉敢进皇城”结尾,令李某对多隆阿的才思敏捷和不失国格心折。当年多隆阿有书房三间,藏书1000多卷。为购书,多隆阿有一段动人故事:多隆阿30多岁时,托英那河入海处蔡家村的海船到南京捎书,一年后,这艘海船没能将书捎回,多隆阿又托另一海船捎书。第二年,两船竟同时将他所要的书运回,可多隆阿只备了一份买书钱。于是,便卖掉了家中198亩耕地凑足了书款,并因此博得“好书不惜挥金买”的美誉。诸多传说来自后人对多隆阿的思念与仰慕,亦真亦幻难辨踪迹。作为清朝大文学家的多隆阿,是生活在英那河下游舒穆录氏的骄傲。采访中,孙庆先又拿出一本“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学者乔川石雄编著的《满洲文学兴废考》,浏览此书便可见到:“自乾隆《四库全书》开馆以来……法式善之掌故,多隆阿之考据,丞龄之词,铁保、成新王之书法为可取。”而从当年辽阳张绣江撰写的《多公墓志铭》可得知,多隆阿姓舒穆录,字雯溪,先世长白人,始祖扬古利追封武勋王,世袭一等公。太祖麻穆嘉于康熙二十六年调盛京,遂为岫岩人,六年后其子孙多移居英那河畔。多隆阿所著除有《易原》十五卷外,更有《易图说》一卷,《易蠡》十五卷,《毛诗多识》十二卷,《慧珠阁诗钞》十八卷,《文钞》四卷,《诗话》四卷,同时著有《阳宅拾遗》四卷,《地理一隅》一卷,为满族文人中之博学者。多隆阿的诗才可从下面这首诗中略见一斑:
征人怨(四首选一)伊州唱罢又凉州,衽甲横矛阅几秋。塞上胡儿时浴马,闺中少妇定登楼。心惊绝域雁空渡,目极长河水自流。苦战沙场筋力尽,论功卫霍独封侯。
后来,多隆阿死于战乱。从《多公墓志铭》中,还可以看到描写当时多隆阿从容赴死情景的文字。
咸丰三年八月,朋友何晓枫镇守山西平阳,敌兵攻城甚急,当时何晓枫对在城里的多隆阿说:“兄处宾师位,弟已派人护公,可急去,弟将与此城共存亡。”多隆阿却笑着说:“是何言?愚与君同举拔萃科,君王臣,愚独非王臣乎?且愚闻有闻友在难而赴之者,未闻见友在难而去之者。君能殉城,愚独不能殉友乎?”于是与何晓枫共同守城,最终被俘不屈而死。死前,敌首对多隆阿说:“汝必读书人,可随我无忧不富贵。”而多隆阿却说:“读书人断不为贼!且为贼亦断无好死者,何富贵云也?”他慷慨赴死后,敌首连呼其忠义之士,并令人铺大堂毡包裹多隆阿尸体藏于僻静处。咸丰四年,多隆阿灵柩才辗转运回,葬于卧鹿山东端。
重学读书的家风习俗
以多隆阿为代表的英那河畔舒穆录氏醉心于文化,仅从他们的姓氏演变便可看出端倪:辫子的满语称为“孙撮活”。在满汉文化融合时期,他们就顺理成章地将“孙撮活”中的第一个字代替自己舒穆录的姓氏,俨然是汉族中的一员。而重学读书,早在多隆阿时代就已成为英那河畔舒穆录氏的一种时尚,不但男人读书,女子也是先读书后学女红。那时女子读书成就最大的当数多隆阿的大女儿大甲。据舒穆录氏族谱载:大甲从父读书有成,族中乡试者之课业阅后即知中否,毫厘不爽;通《内经》,善治小儿麻疹、天花。是时无种痘术,却明“引浆”之理,用已出之浆移接于不出处。复能作画。终身未嫁,享年50余岁。而该族男人读书则显得更“火”:与多隆阿同辈兄弟11人,仅3人没有功名;他们的下代21个男丁中仅1人是白丁;孙辈48个男丁没有不知书的。多隆阿重孙辈中又出现了1923年毕业于北大、以画梅蜚声于国内外的孙同九。
后来的英那河畔舒穆录氏人,在延续着祖先生命的同时,也继承了祖先留下来的重学读书遗风,并把这种良好的遗风发扬光大。原小孤山满族镇流传这样一种说法:生活在这里的舒穆录氏没有一家太富裕,但却没有一家没有学问。今天,走进孙堡村多隆阿后人们结族而居的地方,涌入眼帘的是一座座茅草屋,可这里的男女老幼追求文化却如痴如醉。81岁的老人孙庆先已进耄耋之年,仍笔耕不辍,一面对多隆阿事迹进行考证,一面为创办“孙氏文苑”东奔西走。让老人感到欣慰的是,“文革”结束后,他的侄、孙们都一茬茬、一批批走进高等学府。1990年,他的一个侄女孙玉娥考进了南开大学。同族的孙新把二女儿孙亚军供到大学毕业后,又将小女儿孙亚娴送进了北京民族学院,为此孙新背上了上万元的债务。可他却说:“我们的祖宗能卖地买书,我为什么不能借钱供孩子上学?”1995年夏季,当在家度假的孙亚娴问哥哥孙继明将来能否让她考研究生时,憨厚的哥哥说了一句:“考!只要能吃上饭,我和爸爸就供你读到底。咱不能给祖宗丢脸!”也许,正是这“不能给祖宗丢脸”的想法支撑起舒穆录氏每个成员,使他们在贫寒中仍不忘走近文化,并自觉深入文化,让舒穆录氏文化这一现象像一颗璀璨的明珠,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依然闪亮在英那河畔。据这个村一位姓孙的村干部介绍,孙堡村10个自然屯近2000人,到1996年为止,出了40余个大中专生,而当时这个仅有150人的舒穆录氏家族却出了20个大中专学生,占这里所出的大中专学生的一半。近几年,舒穆录氏家族中出的大中专学生,依然在孙堡村遥遥领先。
当记者到孙庆先老人家采访时,看到老人炕头墙上的这样一幅横额:“家声书声永铭罔替”。他说,这幅横额是他在2004年春节的前一天贴上去的。他之所以这样写,就是要告诫多隆阿的更远的后代子孙,无论什么时候,什么条件,都要继承祖先们留下的诗书传家的遗风,并不断地把它发扬光大。他说,这里的舒穆录氏都无意于仕途。即使是多隆阿、孙同九,也是如此。他们重学读书,主要是为了自身的充实,是对文化的自觉崇尚。
心中有张不可触摸的网
沧海桑田,多隆阿的建树已归于历史,并对今天生活在这里的后人们产生着不可抗拒的影响。英那河自西而东从孙堡村南端日夜不停流过,舒穆录氏人自昔日的皇城盛京辗转至此,已历200余年。其间,他们不仅创造了令人瞩目的灿烂文化,还让重学读书的美德在英那河畔源远流长。记者在深入采访中,触摸到了多隆阿第五世孙孙庆先老人心中那张不可触摸的网。
在老人的带领下,记者驱车来到了多隆阿墓地。这里没有一点被作为历史文物保护起来的迹象,早春的野草尚未返青,别人家的苹果树已经栽到了墓门前,原来垒墓门的石头已经很难寻到……在拜过先人后,老人悲从中来,一行行老泪在脸上肆虐:“先人们,晚辈无能,我对不住你们……”在多隆阿和大甲荒凉的坟头,老人说出了自己心底积压了多年的遗憾:自己早就想给多隆阿这位令后人骄傲的祖先修坟,以寄托舒穆录氏后人对他的敬仰,但“文革”中他被批斗抄家根本无法顾及此事,现在想在这里为祖先立一块普通的墓碑,地界狭小又不可能,更何况张绣江为多隆阿写的《多公墓志铭》长达1800字,需要立3米多高的墓碑才能刻下这些字……
在多隆阿的坟头,老人敞开了郁结在心的另一块伤痕。“文革”中老人被抄家时,家中存放的40余种多隆阿著作手稿和10余幅孙同九的画梅真迹被抄走。对文化“痴迷成性”的老人并不为当时吃了多少苦而流眼泪,却为被抄走的书画而心疼。自1978年开始,老人就上书当时的庄河县、大连市、辽宁省及国家文化部,为寻回被抄走的孙同九的画梅真迹和多隆阿的手稿不停奔走。他说,从1978年到现在,他共上书689封。截至目前,他只找回了一张被抄走的祖先收藏的图画,而另一些被抄走的文物却始终不见踪影。尽管各级部门在不同时期对孙庆先的申诉都有结论性答复,但老人依然在为寻回自己失去的书画而努力……
标签:舒穆录,起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