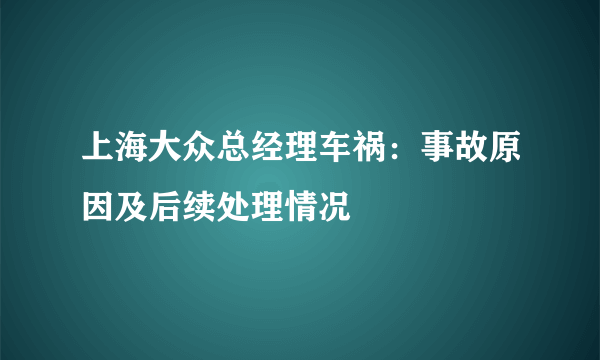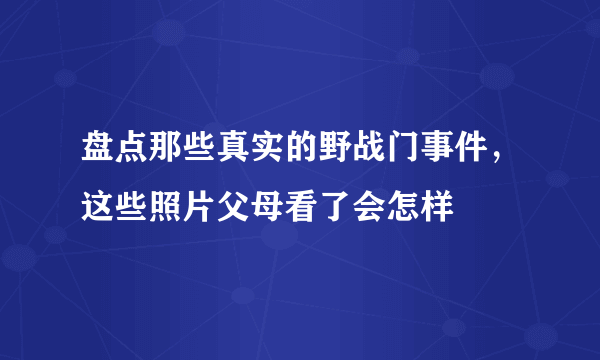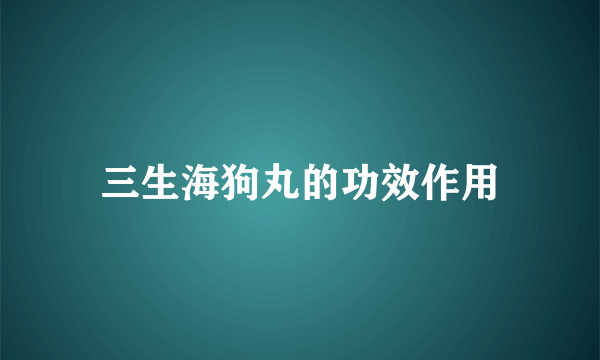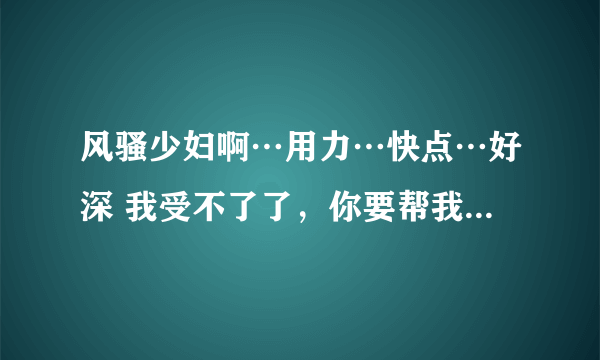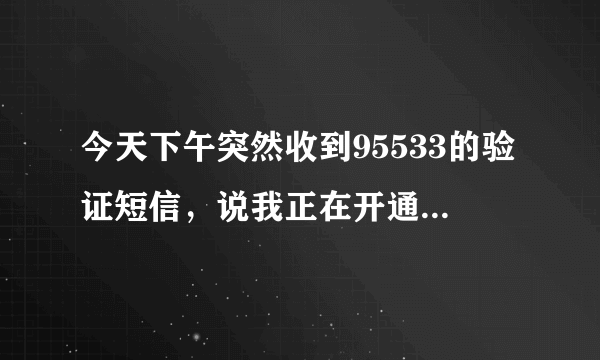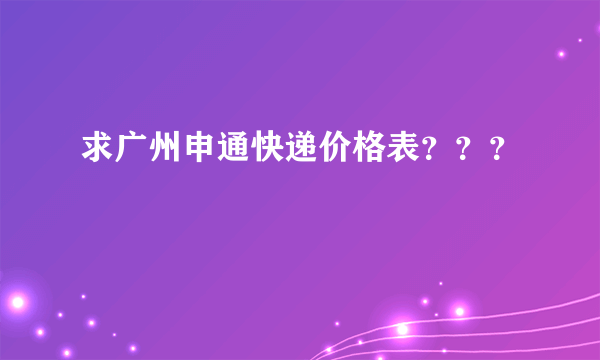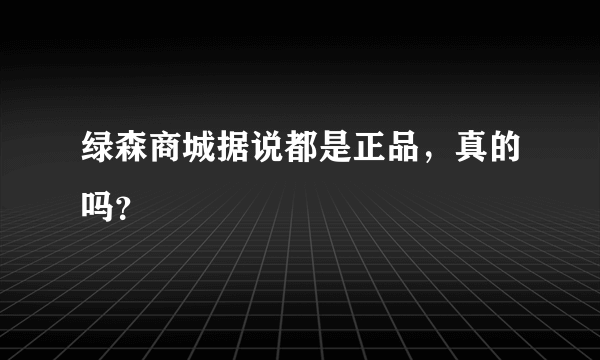▲张斌贤
作者简介: 张斌贤,北京 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钱晓菲,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博士生(北京100875)。
文章来源: 《教育研究》2021年第6期,第70-81页。
摘 要: 杜威与进步主义教育的关系是当代美国教育史研究中充满争议的话题。当前,关于杜威与进步主义教育关系的研究存在“完全关联论”、“部分关联论”和“毫无关联论”三类观点。三类主张都反映了不同时期学界的认识成果,都有其合理性,然而它们未能从具体的和历史的情境中分析杜威与进步主义教育的关系及其变化,因而不同程度地存在瑕疵、不足。基于史实而非推论,从动态和多样性的角度重新考察二者之间的关系,发现杜威教育思想是进步主义教育思潮的重要来源和组成部分,而非其理论基础或指导思想;杜威对进步主义教育运动的批评则缘于对运动方向的调整,而非对运动所倡导原则的否定。杜威与进步主义教育的关系充满了复杂性、多样性和可变性,而非学界以往所认为的是简单的、单一的和静止的。
关键词: 杜威;进步主义教育;进步主义教育思潮;进步主义教育运动;关系分析
杜威(Dewey,J.)与进步主义教育的关系,或者说,杜威在进步主义教育中所扮演的角色,是当代美国教育史研究中一个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这是因为二者同为重要的教育历史现象,杜威是20世纪美国最为著名的教育家,进步主义教育是20世纪美国最具影响的教育思潮,二者都曾产生过广泛而持久的世界性影响,且二者之间的关系又是深入研究杜威和进步主义教育 1 的关键因素之一。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大半个世纪里,中美学者相继就此问题提出了一些主张,但见仁见智,莫衷一是。与此同时,虽然诸多有关杜威和进步主义教育的论述都会或多或少地涉及二者之间的关系,但少有学者对此问题进行专门和系统的探讨。由于上述原因,二者之间的关系至今仍然是一桩悬而未决的“公案”。
本文拟在分析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梳理相关文献史料,从杜威与作为一种社会思潮的进步主义教育之间的关系,以及杜威与作为一种社会运动的进步主义教育之间的关系两个方面入手,从这些关系变化的角度具体分析杜威与进步主义教育之间的关系,以求获得新的认识。
一、学术史梳理
根据相关文献调查,在美国,将杜威与进步主义教育之间的关系当作一个专门的学术探讨的话题始于1959年。这一年恰逢杜威诞辰百年,《学校评论(The School Review)》杂志发行纪念专刊,其中刊登了时任芝加哥大学校长的金普顿(Kimpton,L.A.)和教育史学家克雷明(Cremin,L.A.)撰写的两篇专门讨论杜威与进步主义教育关系的论文。而在我国,类似的探讨则发端于20世纪80年代初。1980年,有学者在《评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一文中涉及了这个问题。 自那时以来,关于杜威与进步主义教育关系的研究一直处于时断时续的状态。综合分析两国学者的研究结论,可以分为“完全关联论”、“部分关联论”和“毫无关联论”三类。
“完全关联论”的核心观点认为,杜威教育思想是进步主义教育的理论基础、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 2 “美国19世纪末兴起的进步教育运动,以杜威的理论为旗帜” ,进步主义教育是杜威实用主义思想在教育中的应用 。由于这个原因,杜威常被认为是进步主义教育运动的创始人、先驱和领袖,是“进步主义教育运动之父”。 3 另一种有着细微差别的观点则认为,进步主义教育是杜威一生诸多成就之一。 简言之,根据“完全关联论”的观点,杜威教育思想是进步主义教育的唯一的或主要的理论基础,他与进步主义教育之间事实上存在着一而二、二而一的密切关系,二者甚至是“同义词”。 在这三类观点中,“完全关联论”在教育学术界占有优势地位。
“部分关联论”实际上是“完全关联论”的衍生和“变种”。这种观点强调杜威与进步主义教育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其中,“联系”(杜威教育思想作为进步主义教育的基础)是前提,而对“区别”的理解则因人而异。一种观点认为,杜威在不同时期对进步主义教育采取了不同的立场。例如,有学者认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他(杜威)是批判传统教育的领袖,他的名字和‘进步教育’几乎成为同义语。到了20世纪30年代,他对进步教育运动出现的一些极端片面的东西不断提出强烈的批评,以致人们称他为‘拒不承认的进步教育之父’” 。另一种观点则主张,不能把进步主义教育运动所推行的一切,如“活动课程”、“创造性的自我表现”、“适应生活”,等等,都归于杜威。但应当说,杜威也是有份的。至少,杜威的写作技巧是拙劣的,他所表述的许多含糊不清的基本概念,往往令人捉摸不定,引起误解。 与此相类似的观点认为,杜威早期思想中确实存在着一些较为激进的主张,因此,他对进步主义教育运动所造成的消极后果负有一定的责任,但不能因此把进步主义教育运动的一切“过错”都归结为杜威的影响。
“部分关联论”还有一种表述形式是,既强调杜威教育理论对进步主义教育的指导作用,又分析杜威从进步主义教育所得到的“益处”。“虽然进步教育运动在某种程度上是以杜威的教育哲学为它的理论指导,但与此同时,杜威无疑也从进步教育运动中为他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体系的形成汲取了养料。在对进步教育运动的肯定、批评和反思过程中,杜威不仅更深入地思考了教育问题,而且也进一步完善了他自己的教育理论。”
“应该看到,进步教育运动的兴起和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也为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在美国扩大其影响和在世界上的传播创造了一个有利的外部环境。”
“毫无关联论”则完全否定杜威与进步主义教育存在实质性的联系,例如,有学者认为,杜威“对轰轰烈烈的进步主义教育运动并未表示过多的热情,他自身也从未承认自己是进步主义教育运动者。” 有学者虽然指出杜威思想与进步主义教育的“契合”,但是更强调二者的差异。 另有学者强调,从20世纪20年代以后,杜威就不再是进步教育运动的解释者和综合者,而是渐渐变成了它的批判者。 伯内特(Burnett,J.R.)则坚称,“如果有人认为杜威是进步教育之‘父’,‘祖父’,或‘老一辈的政治家’,并且认为进步教育工作者是杜威思想的解释者和运用者的话,那么这是对杜威的严重的弯曲。 ”杜威的传记作者马丁(Martin,J.)甚至认为,因为“进步主义教育”这一理念,杜威至少承受了60年甚至更久的谴责,但这一理念根本不是他提出的” 。
“毫无关联论”的另一种表述认为,杜威与进步主义教育的关系是一系列偶然因素所造成的“误解”的结果。较早提出这种观点的是金普顿。早在1959年,他就在《杜威与进步主义教育(Dewey and Progressive Education)》一文中指出,杜威之所以被当作进步主义教育的始祖和先知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他“不幸被广泛地误解了”。直到晚年,杜威才意识到发生了什么,并且几次努力纠正已经产生的误解。 单文经也同样持“误解”的观点,但他的理由是,由于杜威在《民主主义与教育(Democracy and Education)》一书的第六章使用了保守的教育与进步的教育(Education as Conservative and Progressive)的对照,尤其是因为杜威在1928年接受了进步主义教育协会的邀请 4 ,出任该会的名誉会长,所以被误认为是进步主义教育的代言人,二者被画上了等号。
在杜威与进步主义教育的关系问题上,克雷明无疑是着力最多的美国学者之一。1959年,在纪念杜威诞辰百年期间,克雷明发表了《杜威与进步主义教育运动,1915—1952年(John Dewey and the Progressive-Education Movement,1915—1952)》一文,从多方面讨论了杜威与进步主义教育运动之间的关系。 这些观点在他两年后出版的《学校的变革(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School)》这部有关进步主义教育的经典著作中得到进一步阐发。克雷明指出,由于在芝加哥大学创办实验学校和出版《学校与社会(The School and Society)》等著作,“杜威在进步主义教育运动初期起了作用。” 此后十余年中,杜威先后发表了《明日之学校(School of Tomorrow)》等一系列重要著作,“开始为广大具有进步主义思想的公众所知。到1916年,杜威已被公认为进步主义的一位最主要的发言人” 。克雷明强调,在《民主主义与教育》一书的结尾部分,杜威对进步教育运动作了最明白、最全面的阐述。 而在“20世纪20年代之后,杜威很少成为进步教育运动的解释者和综合者,而渐渐成为它的批评者” 。可以看出,在杜威与进步主义教育之间的关系问题上,相比其他学者,克雷明的分析更为具体,也更为丰富,尤其是他注意到这种关系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变化,因而更符合历史的真相。与此同时,克雷明的结论也非常谨慎,他强调杜威理论赋予进步主义教育以一种完整性,从而成为其“代言人”,但并未使用诸如理论基础或指导或进步主义教育之父等诸如此类的表述。
二、重新探讨的“方法论”
回顾已有的研究成果,无论是“完全关联论”或“部分关联论”,还是“毫无关联论”,一方面,它们都是不同论者从自身特有的视角提出的见解,都有其合理性,反映了不同时期学界的认识成果,在不同程度上为后续研究做出了贡献;但是另一方面,由于它们大多未能从具体的和历史的情境中分析杜威与进步主义教育的关系及其变化。因而,三类主张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瑕疵、不足,或者失之片面,或者囿于绝对,因此都难以成立,至少是依据不足。
具体言之,“完全关联论”的主要缺陷在于将杜威与进步主义教育关系简单化和绝对化。在缺乏对进步主义教育深入研究的前提下,不恰当地将其当作一个统一的整体,完全忽视了其中存在的巨大多样性、差异性和复杂性,这便难以准确地把握这种关系。与此同时,“完全关联论”者既没有关注进步主义教育本身的变化,也忽视了对杜威与进步主义教育关系变化的考察,在缺乏充分论证的前提下断言杜威哲学和教育思想为进步主义教育提供了理论基础,甚至将二者相互等同,这种结论既缺乏逻辑,也与史实不符。“部分关联论”的不足则是将杜威与进步主义教育的关系模糊化。这种观点的目的实际上是期望在杜威和进步主义教育之间进行“切割”,以免杜威受到进步主义教育运动失败的“牵累”,因此看似客观、辩证,却带有明显的“抑”进步主义教育而“扬”杜威的倾向,并无助于真正深入地分析二者之间的关系。更为重要的是,虽然确实如“部分关联论”者所强调的那样,自20世纪20年代后期开始,杜威曾多次对进步主义教育提出批评甚至往往是非常严厉的批评,但这究竟说明什么问题呢?这是否就意味着杜威对进步主义教育的否定,是否意味着他与进步主义教育的决裂,因而意味着可以对二者进行切割?由于并未做出具体的分析,“部分关联论”实际上是将这种关系做了模糊化处理,并无助于形成对问题的清晰认识。“毫无关联论”既有“完全关联论”的简单化和绝对化的特点,又带有“部分关联论”的“抑”进步主义教育而“扬”杜威的倾向。之所以“罔顾史实”地否定二者之间客观存在的关系,其目的无非是为杜威“撇清”。这种立场同样无助于客观地认识二者之间的复杂关系。
为真正深入、客观、全面地审视杜威与进步主义教育之间的关系,有三个关键的思想方法问题需要解决。第一,从史实而非推论、客观证据而非主观偏好出发把握这种关系。如果广泛研读相关历史文献,上述三类观点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一些并非从史实出发而仅凭主观偏好的情况,或者是重判断而轻证据的现象。第二,从动态而非静止、历史的而非抽象的视角审视这种关系的形成和变化。从1896年创办芝加哥大学附属学校(“杜威学校”)到1952年为克拉普(Clapp,E.)《教育资源的使用(The Use of Resources in Education)》一书作序,杜威与进步主义教育之间的关系前后持续了半个多世纪。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二者之间的关系发生了一系列复杂的变化,杜威在进步主义教育思潮的传播和进步主义教育运动开展中所扮演的角色也出现了显著的不同。而正是这些变化和差异,构成了杜威与进步主义教育关系的基本内涵。如果仅仅关注某一个时期或以静止的观点分析这种关系,难免失之偏颇。在这方面,克雷明的《学校的变革》虽然提供了一个值得效法的范例,但仍有继续努力的空间。第三,从复杂而非简单、多样性而非单一性的角度考察这种关系。这也就是说,由于进步主义教育本身的巨大复杂性和多样性,因此,只有当明确界定杜威与哪一个进步主义教育的关系,才有可能真正把握二者关系的核心。这就意味着首先应当对进步主义教育进行深入挖掘。
进步主义教育向来被认为是极其复杂的历史现象。“进步主义教育”一词常被认为是英语词语中含义最为模糊、最易产生歧义的教育概念。 在进步主义教育大行其道、进步主义教育运动方兴未艾之际,包括杜威、克伯屈(Kilpatrick,W.)、博德(Bode,B.)、柯布(Cobb,S.)和拉格(Rugg,H.)在内的进步主义教育家都曾致力于揭示其基本的特征。20世纪60年代后至今的大半个世纪里,克雷明、卡茨(Katz,M.)、泰亚克(Tyack,D.)、格拉哈姆(Graham,P.A.)、克里巴德(Kliebard,H.M.)、拉维奇(Ravitch,D.)和里瑟(Resse,W.)等人又相继从不同方面和不同角度对进步主义教育展开讨论,形成了丰富的然而却充满歧义的结论 ,以至于克鲁格(Krug,E.)、克里巴德、甘森(Gamson,D.)和拉维奇(Ravitch,D.)等人甚至认为它是不可定义的。 尽管如此,如果追溯其缘起,辨析其与同时期其他各种教育思潮和教育改革运动的相异之处,有可能厘清进步主义教育的基本特征,从而为进一步分析杜威与进步主义教育的关系打下坚实的基础。
众所周知,从19世纪后期开始,随着美国社会的巨大变迁,在美国社会中逐渐形成了批评、指责和反对以形式主义、机械训练和严酷纪律为特征的旧教育的趋势。与此同时,在卢梭(Rousseau,J.-J.)、裴斯泰洛齐(Pestalozzi,J.H.)、赫尔巴特(Herbart,J.F.)和福禄倍尔(Fröbel,F.W.A.)等欧洲教育家思想的影响下,包括帕克(Parker,F.W.)的昆西实验(1875—1880年)和库克师范学校实习学校实验(1883—1901年)以及杜威的芝加哥大学附属学校实验(1896—1904年)等旨在革除教育中的陈规陋习的实践探索也相继展开。进入20世纪后,一批探索新教育的新型学校在各地先后建立,诸如库科(Cooke,F.J.)的帕克学校(1901年)、梅里亚姆(Meriam,J.L.)的密苏里大学附属小学(1904年)、约翰逊(Johnson,M.)的有机教育学校(1907年)、史密斯(Smith,E.R.)的公园学校(1912年)、普拉特(Pratt,C.)的城乡学校(1913年)、诺姆伯格(Naumberg,M.)的华尔登学校(1915年),等等。目前尚未有确切的统计数据说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究竟有多少所类似的新学校。据杜威父女《明日之学校》中的报道,1915年前后,全美至少有18个新学校或新教育的实验。
这些在当时尚未定名被泛称为“新学校”、“明日之学校”或“进步主义学校”的学校虽然都具有各自不同的特征,但并不排除它们之间存在着一些共性。其中主要包括:强调儿童在教育过程中的地位;注重儿童身体发展,将身体发展当作一切发展的基础;重视兴趣和活动在学习中的作用,等等。这些共性不仅反映了它们区别于同时期其他教育思潮和运动的显著特征,而且构成了日后被称为进步主义教育的基本思想要素。因而,这些学校的出现标志着作为一种社会思潮的进步主义教育思潮的形成。
由于社会思潮具有自发性、流动性、弥散性等特征 ,因此它常常是无形的。而要使那些抽象的观念变成一种可见的存在,关键在于获得一种足以体现观念内涵的物质形式、一种“象征”。有多种途径和方式构建这些“象征”,而集体的有意识的努力和行为无疑是一种恰当的方式。当一些人为追求改变现状而开展集体行动的时候,就产生了社会运动。虽然社会学家对何谓“社会运动”众说纷纭 ,但组织的建立或组织化程度是公认的识别社会运动的重要标志之一。在这个意义上,1919年成立的进步主义教育协会(Progressive Education Association)具有特殊意义,它是进步主义教育从一种社会思潮转化为一个社会运动的重要标志。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因为进步主义教育协会所倡导的基本原则充分反映了进步主义教育思潮的追求。格拉汉姆(Graham,P.A.)指出,进步主义教育协会与进步主义教育至少在五个重要方面具有共同的基础:坚信教育以儿童为中心;坚信学校的社会责任;坚信需要发展一种进步教育的哲学;注重研究;支持者特征同质化的倾向。 另一方面,正是由于进步主义教育协会的成立,使得进步主义教育那些经常模糊的志向制度化,并且将其不明确的宗旨转变为教育的规则。 事实上,直到进步主义教育协会成立,“进步主义教育”才真正成为一个专有名词。 正是由于协会的成立,“人们才公认有这样一场(进步主义教育)运动” 。进步主义教育协会因此成了进步主义教育运动的代言人。
进步主义教育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和作为一场社会运动,既有存在形态的不同,也有历史阶段的差异。从具体史实看,杜威与作为一种社会思潮的进步主义教育的关系(关系Ⅱ)不同于他与作为一场社会运动的进步主义教育的关系(关系Ⅲ)。从关系形成的时间看,前者发生在先,而后者则始于杜威出任进步主义教育协会名誉会长。从关系的形式和内容看,也存在着较大的不同。而正是这两种不同的关系构成了杜威与进步主义教育的关系全部(关系Ⅰ)。由此也说明,杜威与进步主义教育的关系是复杂的、变化的。这样的分析视角不仅符合史实,更大的益处是有助于具体和深入地揭示杜威与进步主义教育关系的复杂性,从而避免绝对化、简单化和模糊化的弊端。
三、杜威与进步主义教育思潮的关系
那么,杜威与进步主义教育思潮的关系(关系Ⅱ)究竟是怎样的呢?
第一,进步主义教育思潮早于杜威教育思想的形成。
在1894年杜威任教芝加哥大学、开始构建其教育理论之前,欧洲教育家的思想正在美国广泛传播。与此同时,帕克已因昆西学校和库克师范学校实习学校的改革而享誉全国,而霍尔(Hall,S.)推动的儿童研究运动正如火如荼地开展,他们的思想与实践不仅是进步主义教育思潮的早期形态,而且直接影响了大批日后被称为进步主义教育家的探索。虽然尚未有证据表明杜威教育思想曾受到帕克或霍尔的影响,但杜威对他们的工作并不陌生。杜威曾在霍普金斯大学直接受教于霍尔,并受其心理学思想的影响。 而在芝加哥大学任教期间,杜威不仅参观了库克师范学校的实习学校,对那里的实验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并先后将自己的子女送入该校,还曾以自己的方式支持帕克的工作。 杜威也高度评价帕克对进步主义教育的贡献。在《新学校究竟有多少自由(How Much Freedom in New School?)》一文中,他明确指出,“帕克上校比其他任何人都更称得上是进步主义教育运动之父” 。
第二,进步主义教育思潮独立于杜威而形成。
由于是自发出现的教育探索,早期的进步主义学校实验的思想来源是非常复杂多样的,不存在某一个统一的思想基础。在早期的新学校实验中,沃特(Wirt,W.)的葛雷制可能是为数不多的主要受到杜威思想影响的教育实验。记者伯恩(Bourne,R.)认为,在葛雷学校,杜威哲学得到了最完整和值得钦佩的运用。 至于其他实验的理论基础则各有各的来源。库科的帕克学校实验的理论基础无疑是帕克的教育思想;密苏里大学附属小学实验的原则主要基于梅里亚姆基于自身实践和理论研究而形成的教育思想;约翰逊的有机教育学校的理论来源则包括理学家奥本海姆(Oppenheim,N.)的儿童发展理论、亨德森(Henderson,C.H.)的有机教育理论、卢梭的自然教育思想、福禄贝尔的“自发活动观念”以及杜威的社会哲学;诺姆伯格虽然在哥伦比亚大学曾受业于杜威,但其思想来源主要是弗洛伊德(Freud,S.)和蒙台梭利(Montessori,M.)等人,而且她并不赞同杜威的某些观点。 如此等等。关于这个问题,柯布早就强调说,“我要特别强调的是,这场在全国各个实验学校进行的进步主义运动是自发的,来自不同的来源,彼此完全没有联系,不能归结到任何一个教育家” 。这也就是说,由于进步主义教育思潮的理论基础存在着诸多差异,并没有一个共同的来源和基础,很难做出杜威教育哲学是进步主义教育思想基础的判断,或者说这个判断至少是不充分的,没有足够的史实依据。
第三,杜威教育思想是进步主义教育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19世纪90年代到1916年,既是进步主义教育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关键时期,也是杜威教育思想的形成时期。从任教芝加哥大学开始,杜威即致力于教育问题的研究和教育实验,开办了芝加哥大学附属学校,先后出版了《兴趣与意志训练的关系(Interest in Relation to Training of the Will)》、《我的教育信条(My Pedagogic Creed)》、《学校与社会》、《儿童与课程(The Child and Curriculum)》和《民主主义与教育》等大量著作,构建了完整的教育理论体系。虽然不能够将杜威教育理论与进步主义教育思潮混为一谈,但是至少在许多基本的问题上,二者具有重要的联系,甚至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杜威关于教育、学校、儿童、教师和教材等方面的论述丰富、充实和提升了进步主义教育的原则。杜威的著作,尤其是他的《民主主义与教育》一书,“把进步教育运动的许多不同方面结合到一种范围广泛的理论之中,并使它们统一,为它们指出方向。正是它的出版,为教育革新运动带来了新的活力” 。
第四,“杜威学校”树立了进步主义学校的样板,扩大了进步主义教育的影响。
1896年,杜威创办了“大学初等学校”(University Elementary School),1902年更名为“芝加哥大学实验学校”(Chicago University Laboratory School),一般称“杜威学校”(Dewey School)。与帕克等人开办的学校不同,杜威学校的理论基础是杜威基于其哲学和心理学所形成的一些假设,其中包括以下几方面。一是,如何使儿童的家庭生活与学校教育更密切地联系起来;二是,如何使儿童在学校中学到的知识与他的经验相互联系;三是,如何激发儿童学习知识和技能的动机、兴趣;四是,如何使教材和儿童的活动相联系;五是,如何处理发展个性与社会合作的关系,等等。 尽管“杜威学校”只存在了八年,并且没有任何直接的继承者和效仿者,但它的作用不容忽视。对杜威本人而言,这所学校验证了关于教育基本问题的假设,为其日后建构完整的教育理论体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进步主义教育而言,“杜威在芝加哥大学的那些年里,‘杜威实验学校(Dewey's Lab School)’成了教育界的一个著名词语,‘进步教育’也成了一个家喻户晓的词语” 。更为重要的是,作为第一所真正意义上的、计划周全的进步主义学校,在以后的岁月中,它的基本原则、课程和方法对进步主义教育运动产生了广泛和深刻的影响。
第五,杜威是进步主义教育思潮的重要传播者。
进步主义学校的相继建立,除了吸引部分学生家长和关心教育事务的社会人士的关注之外,还引起了一些媒体的注意,《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科学美国人(Scientific American)》、《论坛(Forums)》、《文学文摘(Literary Digest)》和《新共和(New Republic)》等报刊都曾报道帕克、约翰逊等人的实验。1913年前后,应达顿出版社编辑约翰逊(Johnson,B.)的邀请,杜威与其女伊芙琳(Dewey,E.)在广泛调查的基础上,完成了《明日之学校》一书,并于1915年出版。尽管杜威在该书的序中强调作者只是对“随意选择的”学校的工作进行描述 ,但因作者准确记录了这些学校独特的多样性,尤其深入分析了这些学校改革背后的理论基础和社会动因,因此,它比任何其他书籍都更引人注目地表达了进步教育运动的信念和乐观主义。 不到十年,《明日之学校》就重印了14次。这种情况在当时是非常罕见的,而在教育类的图书中则是前所未闻的。
综上所述,杜威与进步主义教育思潮之间的关系(关系Ⅱ)是杜威与进步主义教育关系(关系Ⅰ)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关系Ⅰ的早期存在形态。杜威与进步主义教育思潮的关系既非“完全关联论”和“毫无关联论”所认为的那样绝对,也不是“部分关联论”所强调的那样简单、模糊,而是具有丰富多样的含义及其不同的表现形式。在进步主义教育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存在的年代里,杜威的教育思想是进步主义教育思潮的重要来源和重要组成部分,直接丰富了这种思潮的内涵。与此同时,通过实践探索和推广传播,杜威为进步主义教育思潮不断扩大其影响发挥了独一无二的关键作用。待到《民主主义与教育》出版之际,杜威成为进步主义教育当之无愧的、最有影响力的代言人。但不论怎样评价杜威在进步主义教育早期历史中的功绩,都不能以偏概全地断定杜威是进步主义教育之父,同样也难以得出杜威教育思想是进步主义教育思潮的理论基础或指导思想这样的结论,至少没有确定的史实能为这个结论提供充分和客观的佐证。
四、杜威与进步主义教育运动的关系
相比与进步主义教育思潮的关系,杜威与进步主义教育运动的关系(关系Ⅲ)看似简单明了,但实际上却非常复杂。这是因为,一方面,这种关系看似非常重要。从1927年开始直到1952年去世,杜威一直担任进步主义教育协会的名誉会长。在“理论”上,他与进步主义教育运动的关系持续时间长达25年,而进步主义教育协会及其所代表的进步主义教育运动本身也只存在了36年。另一方面,虽然杜威担任名誉会长长达25年,但他对协会少有实际的影响,为数极少的一次影响出现在1928年。在这年的年会上,杜威发表了《进步主义教育与教育科学(Progressive Education and the Science of Education)》的演讲,对进步主义学校的某些倾向提出批评,呼吁探索一种完整的教育理论。 作为回应,协会组成了一个委员会,负责修订协会业已颁布的“进步主义教育七项原则”。该委员会的主要工作成果是在原有“七项原则”的基础上,增加了注重社会发展与纪律、提供优美的环境、强调课程应基于儿童与青年的本性和需要等三条原则,从而构成了进步主义教育协会的“十项原则”。 但这些原则日后并未真正被普遍认可。再一方面,进步主义教育协会的负责人柯布曾强调,协会以杜威教育思想为指导 5 ,但这种声明究竟是真情实意的表达,还是一种宣传或公关策略,其实是值得深究的。这是因为,同样是柯布,日后又强调进步主义教育运动思想来源的多样性。 这实际上说明,至少在部分进步主义教育协会负责人的心目中,杜威其实只是被当作协会的装饰物,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符号”。而杜威本人虽然并未将名誉会长看作很高的荣誉,但始终又没有明确否定他与协会之间的这种关系。所以,不论杜威本人是否愿意,不论客观事实如何,他与协会以及协会所代表的运动之间总是存在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这便为后人留下了巨大的想象或评论的空间。
因缺乏一手史料,目前很难充分了解杜威担任进步主义教育协会名誉会长的具体经过。1927年4月,进步主义教育协会执行委员会致信杜威,邀请他担任名誉会长,并且强调“您比任何人都更能代表我们协会所主张的哲学思想” 。查阅杜威1926—1928年的书信,并未发现他与进步主义教育协会负责人讨论此事的往来书信,仅见1928年2月27日杜威给进步主义教育协会的主要发起人、后任协会第三任会长柯布的简短回信(编号04909),其中写道:如果3月1日前他有时间的话,他会和出版商“说几句话”(get a few words)。 因未见柯布2月9日致杜威的信函,所以难以知晓具体事宜,但至少与协会事务无关,甚至都没有提及十天后杜威即将在协会年会上的演讲(《进步主义教育与教育科学》)。几年后,柯布撰文回忆协会最初十年的经历。他在回忆邀请前哈佛大学校长埃利奥特(Eliot,C.W.)出任协会会长的过程时,叙述较为具体详细。但不知何故,在谈到杜威出任名誉会长的经过时,却语焉不详,几乎是“一笔带过”。
查阅《进步主义教育》杂志1927年后各期所刊登的有关协会活动的报道,可以发现,除出席进步主义教育协会1928年3月8日在纽约举办的第八届年会并发表《进步主义教育与教育科学》的演讲之外,杜威几乎没有参加过协会的任何其他活动。尽管如此,在此后长达二十多年的岁月里,杜威比其他任何人都更为关注进步主义教育运动的进展,一方面不断抵御来自保守主义者的攻击,捍卫进步主义教育的基本原则;另一方面又不时批评进步主义教育运动中出现的“非此即彼”的偏差。
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永恒主义、要素主义和新托马斯主义的教育家开始从不同方面指责和抨击进步主义教育,这其中包括赫钦斯(Hutchins,R.)、阿德勒(Adler,M.)、巴格莱(Bagley,W.)、米克尔约翰(Meiklejohn,A.)和马里坦(Maritain,J.)等。永恒主义者以理性发展的目的反对个性发展的目的。他们认为,理性是人的最高属性,理性的发展应当成为教育的最高目的。理性比儿童的自由、态度和自我表现更为重要。此外,他们以基础学科反对活动课程。赫钦斯指责进步主义学校为满足学生的一时兴趣,轻视系统知识的教学,片面强调直接经验而放弃传统。他指出,“传统是教育的根本”,“要让受教育者、天才和聪明人取得真正的进步,就必须让他们先掌握传统”。
在《要素主义者促进美国教育的纲领(An Essentialist's Platform for the Advancement of American Education)》中,巴格莱从不同方面分析了美国教育中存在的种种问题,认为造成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是进步主义教育理论这种“软弱的教育理论”的作用。他抨击进步主义教育降低对学生的要求,刻意迎合学生的兴趣从而放弃系统科目的学习,片面强调活动课程而忽视基础知识。 马里坦(Maritain,J.)同样对进步主义教育提出了多方面的批评。
20世纪30、40年代,杜威先后与赫钦斯、米克尔约翰(Meiklejohn,A.)等人展开论战。他首先反击赫钦斯等人的观点,指出永恒主义者所强调的“永恒学科”、古典课程,只能使学生与不断变化的社会相脱节,从而使学校成为一种守旧、落后的机构。在《为什么有进步主义学校(Why Have Progressive Schools?)》(1933年)一文中,杜威批驳了对进步主义教育的种种责难。他强调指出,当前许多对进步主义学校的批评缘于批评者沉迷于旧的教育模式和对新事物的抗拒。针对一些批评者对进步主义学校自由散漫的指责,杜威指出,与旧学校不同,进步主义学校所追求的并不是整齐划一的秩序,而是学生以及学生团体自由探索的氛围。有批评者指责进步主义学校盛行个人主义哲学,杜威反驳道:进步主义学校所强调的恰恰是使个性解放与社会责任的平衡。
在不断回击保守主义攻击的同时,杜威也时刻对进步主义教育运动中出现的各种偏差、错误提出批评,而且往往是非常直接的和严厉的批评。“几乎没有批评家对‘进步教育’的评论像杜威一样,非常严格和公正地指出它目前存在的缺陷。”
从20世纪20年代后期开始,杜威先后发表了《进步主义教育与教育科学》(1928年)、《新学校有多少自由》(1930年)、《教育与当前的社会问题(Education and Our Present Social Problems)》(1933年)、《需要一种教育哲学(The Need for a Philosophy of Education)》(1934年)和《经验与教育(Experience and Education)》(1938年)等著述,在努力为进步主义教育运动辩护的同时,也冷静地分析了运动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并且指出了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途径。
杜威尖锐地指出,进步主义教育运动存在的根本缺陷是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即当它抛弃它将取而代之的一些目标和方法时,它可能只是消极地而不是积极地、建设性地提出它的原则。因此,在实践中,它是从被它抛弃的东西里获取解决问题的启示,而不是建设性发展自己的哲学,从而寻求解决问题的答案”
。正因如此,进步主义教育运动中往往出现因对旧学校中纪律、秩序、灌输、教师权威、系统知识教学等的恐惧而走向反面,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儿童中心论”就是这种极端的典型反映。杜威认为,进步主义教育运动的进步将取决于克服与生俱来的情感大于理性、重破坏而轻建设的局限,不断地批判性地反思自己的原则。
在《〈教育资源的使用〉引言》这篇平生最后的教育论述中,杜威简要回顾了半个多世纪以来进步主义教育运动的历程,指出运动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分析运动所面临的困难,也充分肯定了运动所取得的重要成就。杜威尤其强调进步主义教育运动产生的历史必然性,他认为,进步主义教育运动是19世纪后期兴起的巨大的思想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推动个人解放的社会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
有学者尤其是“部分关联论”者通常将杜威后期先后发表的一系列评论进步主义教育的著述视作对运动的批评、不满、失望甚至否定,以此对二者进行“切割”,并证明杜威不应为进步主义教育运动的失败承担责任。这实际上是一种表面化的认识。这是因为,虽然同是批评,但绝不能因此把杜威的批评与赫钦斯、巴格莱和马里坦等人的批评混为一谈。赫钦斯等人批评的目的是要否定进步主义教育,而杜威的目的则是对运动的反思,通过指出运动中出现的各种偏差,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使其更好的发展。显然,赫钦斯等人的批评是破坏性的,而杜威的批评则是建设性的,是为了引导运动朝着合理的方向行进。所以,杜威与其说是批评、指责,倒不如说是引导、纠偏。事实上,在进步主义教育的历史上,从没有一个人像杜威一样,几十年如一日,始终不渝地关注进步主义教育事业,既像一位“慈母”,在外界声讨之时,挺身而出予以保护;又似一位“严父”,不时严厉批评运动中出现的各种弊端。简言之,自1927年担任协会名誉会长之后,杜威实际上一直在两条“战线”上作战,既毫不留情地反击保守主义者的进攻,又坚持不懈地致力于调整运动的方向。
杜威与进步主义教育的关系是一种非常复杂的历史现象。既然如此,合理认识这种关系的最佳途径就是将其还原到19世纪末、20世纪前期美国教育的历史进程之中,还原到进步主义教育的历史进程之中。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随着进步主义教育自身从思潮向运动的演变,杜威与进步主义教育的关系无论是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在出任进步主义教育协会名誉会长之前,杜威更多地扮演了进步主义教育的探索者、实践者、传播者和集大成者的角色;而在此之后,杜威则主要发挥了进步主义教育的捍卫者和进步主义教育运动的引导者。经历大半个世纪的多次变化,杜威与进步主义教育的关系获得了多种形式,其内涵也日趋丰富。
参考文献
赵祥麟.评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80,(2).
滕大春.杜威和他的民主主义和教育(下)[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1);吴俊升.教育与文化论文选集[C].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2.292;张斌贤.社会转型与教育变革:美国进步主义教育运动研究[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7;丁永为.杜威[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1;郭九林,梁艳君.美国进步主义时期的教育思想溯源及其社会影响[J].沈阳教育学院学报,2007,(6).
乔治·奈勒.教育哲学导论[A].陈友松.当代西方教育哲学[C].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2.70.
Hopkins,E.A.John Dewey and Progressive Education[J].The Journal of Educational Thought,2017,(1).
赵祥麟.杜威[A].王天一,单中惠.外国教育家评传2[C].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495.
丁永为.变化中的民主与教育:杜威教育政治哲学的历史研究[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2.173;罗伯特·威斯布鲁克.杜威与美国民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175;赵祥麟.杜威[A].王天一,单中惠.外国教育家评传2[C].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495.
吴志宏.美国“进步教育运动”述评[J].外国教育动态,1984,(3).
单中惠.现代教育的探索:杜威与实用主义教育思想[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200、200.
张俊列,金心红.课程·经验·艺术--杜威课程思想的美学意蕴[J].教育学报,2015,(5).
王红丽,张啸鹏.再论杜威与进步主义的关系[J].甘肃高师学报,2017,(5).
刘云杉.兴趣的限度:基于杜威困惑的讨论[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9,(2).
乔·伯内特.如何评价杜威?[A].陈友松.当代西方教育哲学[C].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2.182.
杰伊·马丁.教育人生:约翰·杜威传[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335、46、140、304.
Kimpton,L.A.Dewey and Progressive Education[J].The School Review,1959,(2).
单文经.《经验与教育》一书的重要性[A].杜威.经验与教育[M].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5.81-82.
Cremin,L.A.John Dewey and the Progressive-Education Movement,1915-1952[J].The School Review,1959,(2).
劳伦斯·克雷明.学校的变革[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9.105、107-108、108、211、243、109、136.
Gordon,P.Lawton,D.A Guide to English Educational Terms[M].London:Batsford Academic and Educational,1984.126.
张斌贤.“世纪难题”:什么是进步主义教育[J].教育研究,2020,(3).
Gamson,D.District Progressivism:Rethinking Reform in Urban School Systems,1900-1928[J].Paedagogica Historica,2003,(4);Ravitch,D.The Troubled Crusade:American Education,1945-1980[M].New York:Basic Books,Inc.,Publishers,1983.44;Davis,S.The Paradox of Progressive Education:A Frame Analysis[J].Sociology of Education,2002,(4).
彭涟漪,马钦荣.逻辑学大辞典[Z].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697.
Cook,K.S.,et al.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Social Psychology[M].Boston:Allyn and Bacon,1995.571.
Graham,P.A.Progressive Education from Arcady to Academe:A History of the Progressive Education Association,1919-1955[M].New York:Teachers College Press,1967.145,145,61,51.
罗伯特·威斯布鲁克.杜威与美国民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175、100.
康内尔.二十世纪世界教育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573.
Dewey,J.How Much Freedom in New School?[A].Boydston,J.A.The Later Works of John Dewey(vol.5)[C].Carbondale and Edwardsville: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1984.320.
Bourne,R.The Gary School[M].Boston:Houghton Muffin Co.,1916.144.
Beck,R.H.American Progressive Education,1875-1930[D].New Haven:Yale University,1942.4,4.
凯瑟琳·梅休,等.杜威学校[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18-38.
Rugg,H.Foundations for American Education[M].New York:World Book Company,1947.515.
杜威.学校与社会·明日之学校[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213.
杜威教育论著选[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251-264、431.
Cremin,L.A.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School[M].New York:Vintage Books,1961.249.
Hickman,L.A.The Correspondence of John Dewey(vol.2)[M].Carbondale: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2006.47.
Cobb,S.The Romance of Beginnings[J].Progressive Education,1929,(1).
方展画.赫钦斯[A].赵祥麟.外国教育家评传3[C].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86.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等.现代西方资产阶级教育思想流派论著选[C].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151-155.
洪明.马里坦[A].赵祥麟.外国教育家评传3[C].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201-237.
Dewey,J.Panel Discussion:Education Today[A].Boydsto,J.A.The Later Works of John Dewey,1925-1953(vol.11)[C].Carbondale and Edwardsville: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1987.579-580.
约翰·杜威.我们怎样思维·经验与教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246、246-250.
注释
1国内教育学界通常将英文“progressive education”译作“进步教育”,将英文“progressive education movement”译作“进步教育运动”。在中文语境中,“进步”一词具有明显的褒义或肯定性倾向,通常与“落后”、“保守”等相对,因此,将“progressive education”、“progressive education movement”分别译作“进步教育”和“进步教育运动”,容易产生歧义。本文采用美国史研究中一般的译法,将“progressivism”译作“进步主义”,将“progressive education”译作“进步主义教育”,将“progressive education movement”译作“进步主义教育运动”,以求客观表述。而对所引用的其他学者的表述,则尊重原意,不做变更。
2(1)参见:吴志宏.“美国‘进步教育运动’述评”[J].外国教育动态,1984,(3)。洛克菲勒(Rockefeller,S. C.)认为,“迁移到芝加哥之后,杜威成了这派(进步主义教育)运动的骨干力量”,而“到《民主与教育》出版的时候,杜威已经成为进步主义运动最为重要的哲学家”。参见:斯蒂文·C.洛克菲勒.杜威:宗教信仰与民主人文主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281。韦布(Webb,L. D.)认为,杜威的《民主主义与教育》为一代进步主义教育家提供了理论依据。参见:韦布.美国教育史:一场伟大的美国实验[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 206.
3(2)参见:蒂尔.进步教育果真过时了吗?[A].瞿葆奎.美国教育改革[C].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 220。里帕(Rippa,S. A.)认为,杜威是进步主义教育运动的领导。参见:里帕.自由社会中的教育:美国历程[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 186.
4(1)单文经所说的杜威在1928年接受进步主义教育协会邀请出任名誉会长疑有误。目前虽然尚未有史料说明杜威何时接受协会的邀请,但柯布(Cobb,S.)在《进步主义教育(Progressive Education)》杂志1927年第3期发表的《回顾与前瞻》中就指出,1927年协会最大的收获是杜威同意任职。参见:Cobb,S. Retrospect and Prospect[J].Progressive Education,1927,(3).
5(1)柯布曾明确指出,杜威哲学是进步主义教育的基础。参见:Cobb,S. The 1928 Conference[J]. Progressive Education,1928,(3).
了解作者更多信息请点击阅读原文
推荐阅读:
张斌贤——超越“克雷明定义”:重新理解进步主义教育的出发点
张斌贤:从“体系时代”转向“问题时代”:我国外国教育史学科振兴的路径
於荣,张斌贤:繁荣与调整:战后美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轨迹
陈露茜 张斌贤 石佳丽:近年来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进展
张斌贤 高玲:教育史研究的功用
标签:张斌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