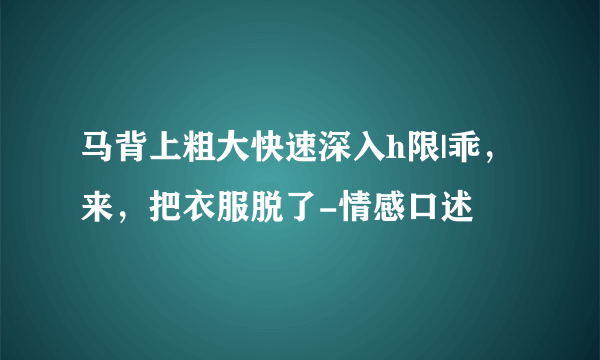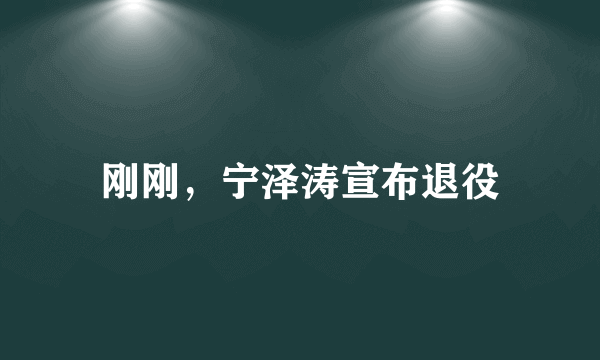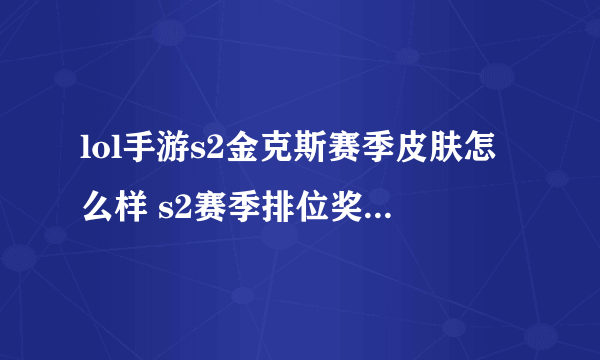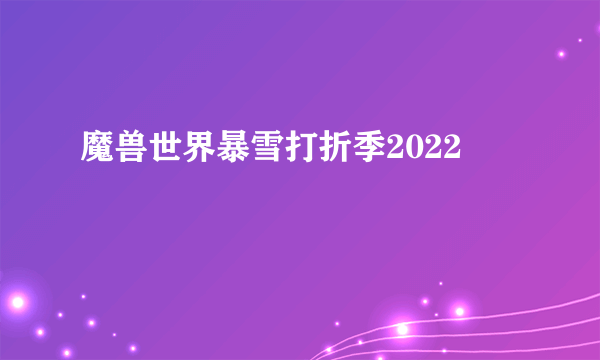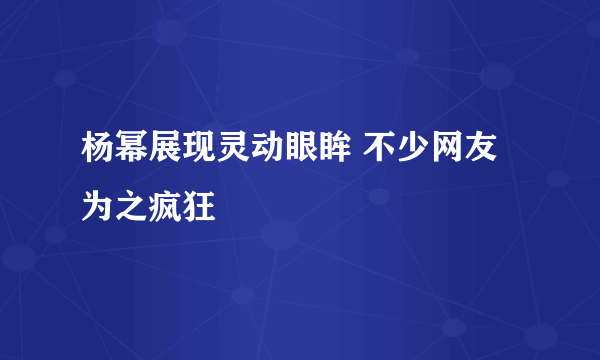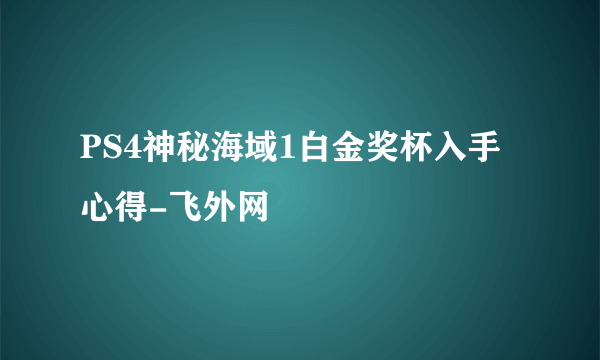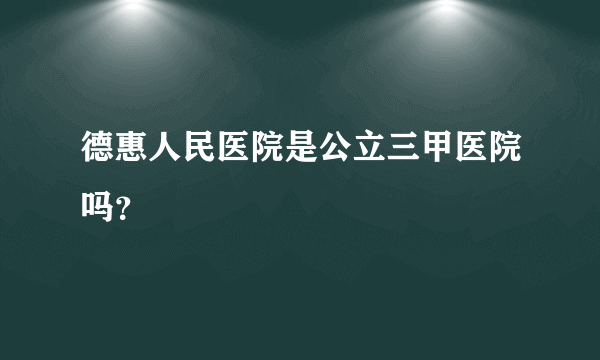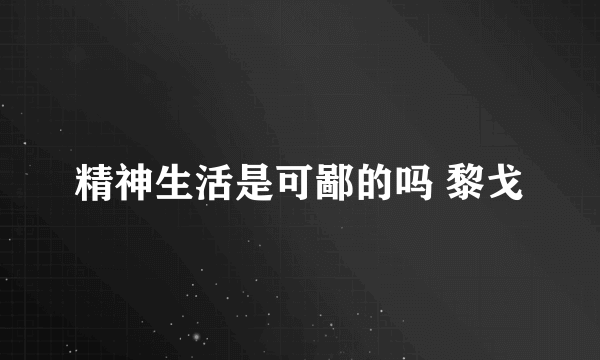
黎戈:精神生活是可鄙的么?一个信任文艺的人,骨子里往往有天真的东西,这个东西,让他们不务实,不适应生活,不够圆熟,合群,也不容易快乐起来——他们多半都是没什么财势的loser,但是也是这个东西,把人的心,距离缩小了。
我这两天在复读托尔斯泰的回忆录,《童年少年青年》,翻译者是草婴,我记得有次在央视看见他被采访,说他在文革里,被打成右派,体重不足一百斤的他,每天要扛一百多斤一包的水泥,有天听到卡哒一声就痛晕过去了,医院诊断结果是十二节胸椎骨折,不好用绷带,也没药,加之他当时的身份,没有资格住院,就是躺床上等死。
草婴仰天躺在块床板上半年,吃喝拉撒都在上面,后来总算腰骨自己痊愈了,但也落下了沉疴。
我想起他翻译托尔斯泰全集,都是在文革之后的事,他是二十年代出生的,当时年过五十了,而他五十岁以后的作品,数量上不亚于他之前所有的精神分泌物。
《东坡志林》里,写苏东坡和儿子被贬海南,搭了个打珠的小船过海,风浪大作,风云压顶,他说了一句话,具体我不记得了,大意是,天若佑我过此关,吾辈必济。
我想草婴这个晚年奋发和苏东坡大难当头时的立誓是一个心意,就是,我见识了生之不易,一定要拿我从老天爷手里夺回的时光,做有益的事。
前一阵子家里有事,情绪非常低落,惶惶不可终日。每天都从家步行到绣球公园,再走回来。布鞋都磨坏了底,水泡变了老茧,最后成了鸡眼一样的角质层。
等到事情慢慢平息,我又开始看书,看杨绛回忆录,她说文革时不觉得苦,因为单位冷落他们,反而可以从容的看书,比沦陷区的时候幸福多了。
这些人,这些事,都让我深深的被打动。因为里面有信,望,爱。
后来猪头把文章拿到老周那边去,他们说不好,喜欢我过去刻薄的笔法云云,大概是觉得我太主旋律了吧,其实我想说的,不是杨绛不畏强敌的高尚品质,而是一个人与书本相亲,那种信任感,给我的感动。
很多人说,要远离文艺,投身生活。我不敢这样说,因为我不是知识分子,我不是知识的拥有者,传播者,或靠他为生的人,不具备这种亲缘关系,所以,对它只好持一颗敬畏之心,不能说它的坏话。
律师可以说司法不公,医生可以说医疗黑幕,劳苦大众可以说劳动低下,人都喜欢荼毒自己手边的东西。
我一朋友从十八岁第一次结婚,屡被骗财骗色,到现在四十出头,没孩子没男人,只剩一个坏掉的子宫,还有一身的情伤。
每次听她说苦难史都让我胆寒……
她与生活耳厮鬓磨,才有底气说生活的坏话。我不太明白,为什么文艺和生活就是敌对,二元的呢?
每年跳大桥寻短见的人,好像都不是知识分子啊,人家没知识,不代表不思考,不钻牛角尖。我一亲戚就因为少加了一级工资,撞车死了。
草婴在文革时翻译过灰皮书,就是一批翻译家,不署名的,每人几章,像流水线一样译出一系列世界名著,这些书,是当时中国仅有的外国文学著作,被多少青年秘密相传,爱若珍宝,染上了孩子们的手汗和轻尘,翻的边角都破烂了啊。
它们,是那个时代仅有的异于主流高大全文学、口号、语录的声音、精神火炬。
八十年代初,文艺作品刚刚解禁时,多少人在新华书店门口排队等着买它们。
草婴他们,就是传递火炬的人。而现在呢,特价书店遍地开花,知识垂手可得,学历人手一张,于是大家撇下嘴角,鄙薄着书本。从什么时候开始,精神生活成为可鄙的事情了呢? 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不是返回俗世或是过精神生活的问题,而是信心。
文艺青年信任文艺,俗世之人畅饮一杯丰腻的世俗之水,求仁得仁,各得其所,信心与爱方向一致,人就会活得快乐浑然。
再看看草婴怎么说:“我对自己所做的事情、所走过的道路,都是无怨无悔的。因为我觉得在每一个历史阶段里,我做了我力所能及的、最应该做的工作,我不曾有过自怨自悔的情绪。我精神上始终没有垮,所以才可以坚持下来。”
我并不想褒扬文艺青年,但是我的文青朋友们,都是非常温暖和真挚的,日常谈笑互娱,患难的时候扶持,就说这次我有麻烦,要给我汇款的,寄东西的,找关系的,坐火车和飞机来看望我的,都有,还有什么忙也帮不上的,就老给我打电话问进展如何,他们让我觉得不孤单。
一个信任文艺的人,骨子里往往有天真的东西,这个东西,让他们不务实,不适应生活,不够圆熟,合群,也不容易快乐起来——他们多半都是没什么财势的loser,但是也是这个东西,把人的心,距离缩小了。
标签:黎戈,可鄙,精神